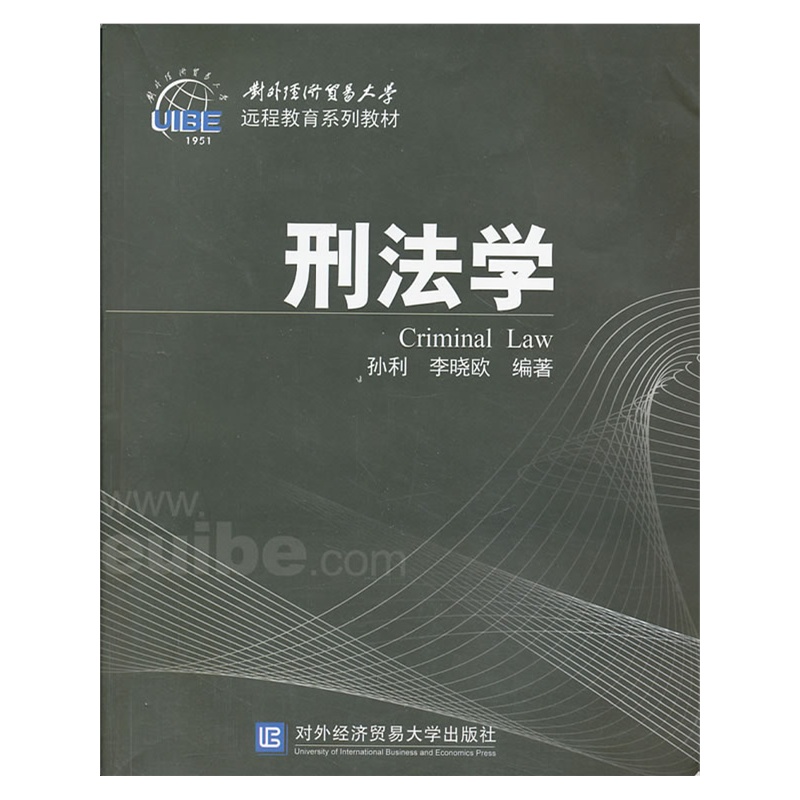
近来,少林寺原方丈释永信被查询事情,不只引发社会对宗教界处理的广泛评论,更在法学领域抛出一个重要出题:
这一问题的背面,是宗教产业特别特点与刑法规制一般性之间的张力——宗教活动场所作为承载崇奉功用的特别安排,其产业既或许触及国家一切的文物、团体土地,也包含信教公民的捐献、自建财物等,而作业人员对这些产业的处理行为是否落入刑法规制规模,必定的联络到宗教产业的保护与刑法谦抑性的平衡。
现行法令体系中,《宗教事务法令》《民法典》虽对宗教产业的权属与处理作出规则,但刑法层面没有针对宗教活动场所作业人员的职务违法作出专门标准,相关司法解说亦存在含糊之处。公安部经济违法侦办局2004年批复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3年答复的效能争议,以及“单位”这一刑法概念在不同罪名中的射程差异,使得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确定常陷入困境。
基于此,本文拟从标准整理动身,以法人资历为中心,结合产业独立性与安排处理性两层标准,证明宗教活动场所作业人员构成职务侵吞罪、移用资金罪的主体适格性,为司法实践供给教义学支撑。
讨论宗教活动场所作业人员的主体适格性,首要需厘清现行相关标准性文件的法令地位。现在触及该问题的文件最重要的包含公安部经侦局的批复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的答复,但二者均非严厉意义上的“法令根由”,其标准效能也有必定限制。
公安部经济违法侦办局2004年《关于宗教活动场所作业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吞或移用资金违法主体的批复》(公经〔2004〕643号)清晰指出:
“宗教活动场所的处理人员运用职务之便,侵吞或移用宗教活动场所公共产业的,可以构成职务侵吞罪或移用资金罪。”但该批复的效能需从两方面审视:
其一,从方式合法性看,该批复由公安部内设安排(经侦局)发布,未遵从《立法法》对部分规章规则的“揭露征求定见、部务会议审议、首长签署发布”等程序,不归于“部分规章”领域,仅为公安机关内部法令辅导文件。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说,公安机关的内部指示对司法判定并无强制适用的效能,仅可起到参照作用。
其二,从内容合理性看,批复将宗教活动场所产业直接界定为“公共产业”,与《刑法》第九十一条对“公共产业”的法定规模存在抵触。刑法意义上的公共产业包含三类:国有产业、劳动群众团体一切的产业、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作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产业。
其间,“公益作业”特指面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福利性作业(如教育、医疗、扶贫等),而宗教活动场所的产业虽或许包含捐献,但捐献意图是服务于宗教活动与信教公民需求,具有特定指向性,与“公益作业”的开放性特征不符。因而,将宗教产业直接归入“公共产业”的定性,缺少刑法教义学依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3年《关于释教协会作业人员能否构成纳贿罪或许公司、企业人员纳贿罪主体问题的答复》(高检研制第2号)指出:
“释教协会归于社会团体,其作业人员除受托付从事公事者外,既非国家作业人员,也非公司、企业人员,不能按纳贿罪或公司、企业人员纳贿罪追究责任。”该答复看似与宗教活动场所相关,但适用上存在两层限制:
一方面,主体规模错位。释教协会归于《宗教事务法令》规则的“宗教团体”,而宗教活动场所(如寺庙、道观)归于“宗教活动场所”,二者虽有几率存在人员穿插(如场所担任人在协会兼职),但法令性质天壤之别:宗教团体如释教协会、道教协会等,是联络信教公民与政府的桥梁,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历;宗教活动场所如白云观、少林寺等,是展开宗教活动的固定场所,其法人资历需独自请求。因而,针对宗教团体作业人员的答复无法直接适用于宗教活动场所作业人员。
另一方面,效能已被代替。该答复针对的当年的“公司、企业人员纳贿罪”(现为非国家作业人员纳贿罪),已被2008年“两高”《关于处理商业贿赂刑事案子适用法令若干问题的定见》(以下简称《商业贿赂定见》)掩盖。《商业贿赂定见》第二条清晰将“社会团体”归入“其他单位”规模,其作业人员可构成非国家作业人员纳贿罪。但需注意的是,该定见仅针对纳贿类违法,且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说作业规则》,研究室答复不归于正式司法解说,在标准意义上不具有遍及约束力。
宗教活动场所作业人员能否成为职务侵吞罪、移用资金罪的主体,中心在于宗教活动场所是否归于刑法意义上的“单位”。而刑法中的“单位”并非肯定概念,其规模因罪名性质、保护法益的不同而存在必定的差异,需结合详细罪名的构成要件进行解说。
刑法用语的相对性原理标明,同一概念在不同条文或金钱中,或许因规制意图不同而具有不一样内在。“单位”这一概念在刑法中即呈现出显着的相对性:
单位违法中的“单位”:作为违法主体,须具有法人资历或准法人资历,且以合法建立、从事合理活动为条件(如《全国法院审理金融违法案子作业座谈会纪要》清晰,为违法而建立的单位或建立后以违法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违法论处)。其间心是“独立承当刑事责任的才能”,规模较窄。
非国家作业人员纳贿罪中的“单位”:作为违法主体所属的安排,规模较宽。《商业贿赂定见》将“作业单位、社会团体、乡民委员会、组委会”等均归入“其他单位”,乃至包含“非常设性安排”。其间心是“存在职务便当的安排载体”,无需具有法人资历。
职务侵吞罪中的“单位”:作为被害目标,是“公司、企业或许其他单位”,其规模介于上述二者之间。职务侵吞罪的保护法益是单位对产业的占有、运用、收益权,因而“单位”须具有两个中心特征:一是产业独立性(具有独立于成员个人的产业);二是安排处理性(存在安稳的处理架构与规章准则)。
这一标准既不同于单位违法中“独立承当刑事责任”的要求,也窄于非国家作业人员纳贿罪中“暂时安排”的规模,需结合详细安排的性质归纳判别。如《商业贿赂定见》中的“依法组成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商洽收购中商洽小组、询价收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能成为非国家作业人员纳贿罪的主体,但无法成为职务侵吞罪的主体。
从职务侵吞罪的立法意图看,其旨在冲击“运用职务便当将单位产业不合法占为己有”的行为,保护单位产业的处理准则。
首要,职务侵吞罪中的“其他单位”也是“单位”的一种形状,应当具有必定的安排性,而不应是自然人独自个别。其次,独立的产业是建立“其他单位”的必备要件——职务侵吞罪保护的法益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物,假如某一安排没有独立的产业,就丧失了运用职务侵吞罪进行法益保护的必要性。
1.产业独立性:单位需具有独立于成员个人的产业,且该产业的分配、运用需遵从单位毅力而非个人毅力。例如,居民委员会处理的团体产业、业主委员会处理的修理基金,均独立于成员个人,归于“单位产业”。
2.安排处理性:单位需存在安稳的处理安排与规章准则,可以对产业进行标准处理。例如,乡民委员会经过乡民会议拟定财政准则,评标委员会经过规章规则作业流程,均具有安排处理性。
据此,宗教活动场所是否归于“其他单位”,需以这两项标准为中心,结合其法人资历状况详细分析。
依据《宗教事务法令》与《民法典》,宗教活动场所分为“已获得法人资历”与“未获得法人资历”两类,二者的产业权属与处理架构不同,其作业人员的主体适格性也存在差异。
《民法典》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则,具有法人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可请求获得“捐助法人”资历;《宗教事务法令》第二十三条进一步清晰,宗教活动场所完结法人挂号后,获得独立民事主体资历。此类场所的作业人员明显归于职务侵吞罪、移用资金罪的适格主体,理由如下:
1.产业独立性齐备: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条,捐助法人“依法一切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令保护”,其产业独立于建立人、处理人及信教公民,场所对产业享有占有、运用、收益和处置的完好权力(除不合法令还有规则,如国有文物的一切权归国家)。
2.安排处理性标准:法人资历的获得以“有必要的产业或经费、有自己的称号、安排安排和居处”为条件(《民法典》第五十八条)。此类场所需建立处理委员会(或相似安排),拟定财政、财物处理等准则,并报宗教事务部分存案(《宗教活动场所处理办法》),悉数契合“安排处理性”要求。
因而,已获得法人资历的宗教活动场所归于刑法中的“其他单位”,其作业人员运用职务便当侵吞、移用场所产业的,可构成职务侵吞罪、移用资金罪。
未获得法人资历的宗教活动场所,其产业权属与处理架构相对杂乱。依据《宗教事务法令》第四十九条及释义,此类场所的产业分为两类:一是国家或团体一切的产业(如国有土地、文物),场所仅享有处理权;二是自有合法产业(如自建房子、捐献收入),由宗教团体或挂号处理机关指定的安排代管。对此类场所的作业人员,需结合“产业独立性”与“安排处理性”判别其主体适格性:
1.具有标准处理的未挂号场所:若场所已经过民主程序建立处理安排(由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代表组成),拟定财物处理准则(如建立公共账户、实施开销批阅),且产业由处理安排一致处理(非个人操控),则契合“产业独立性”与“安排处理性”。未挂号场所假如“在政府监督下对产业来处理”,其处理安排的团体决议计划机制已具有安排处理性,产业亦独立于个人,归于“其他单位”,作业人员可构成相关违法。
2.松懈处理的未挂号场所:若场所未建立处理安排,产业由个人(如住持、担任人)直接操控,缺少标准准则(如收入存入个人账户、开销无批阅),则不契合“产业独立性”与“安排处理性”,不归于“其他单位”。此刻作业人员侵吞产业的,或许构成侵吞罪(针对代为保管的产业)或盗窃罪(针对无保管联系的产业),而非职务侵吞罪。
宗教活动场所作业人员能否成为职务侵吞罪、移用资金罪的主体,需以“产业独立性”与“安排处理性”为中心标准,结合场所的法人资历状况归纳判别:
1.已获得法人资历的宗教活动场所(如少林寺),归于刑法中的“其他单位”,其作业人员运用职务便当侵吞、移用产业的,构成职务侵吞罪、移用资金罪。
2.未获得法人资历但处理标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已建立处理安排、产业独立处理),归于“其他单位”,作业人员可构成相关违法。
3.未获得法人资历且处理松懈的场所(产业由个人操控、无标准准则),不归于“其他单位”,作业人员的行为或许构成侵吞罪或盗窃罪。
司法实践中,可从三方面推动确定标准化:一是严厉检查场所的法人挂号证明及处理准则,承认“单位”特点;二是区别产业性质(国有/团体一切产业与自有产业),对国有产业可优先适用贪污罪(若作业人员受托付从事公事);三是重视实地查询,经过信教公民代表访谈、财政账册核对等,承认产业是否独立于个人。
唯有如此,才能在保护宗教产业安全与保护宗教崇奉自由之间完成平衡,既防止宗教场所沦为“法外之地”,也防止刑法规制过度介入宗教事务,终究完成法令作用与社会作用的一致。
本文声明 本文章仅限学习沟通运用,如遇侵权,咱们会及时删去。本文章不代表北律信息网(北宝)和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令定见或对相关法规/案子/事情等的解读。